【企業(yè)文化】講王陽(yáng)明的故事,話(huà)“度”的人生學(xué)問(wèn)
日期:2020-10-28 閱讀數(shù)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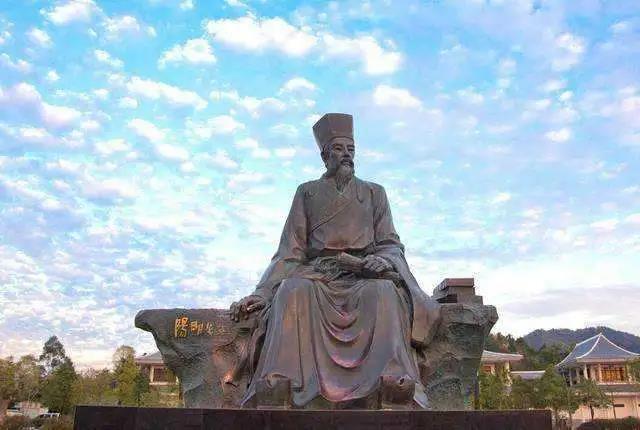
如今,關(guān)注我國(guó)古代先哲王陽(yáng)明的人,是越來(lái)越多。王陽(yáng)明的故事不少,在中國(guó)古代歷史上,已有位置。王陽(yáng)明的智慧對(duì)當(dāng)代的后人頗有啟迪,特別是關(guān)于“度”的觀點(diǎn)。下面我講王陽(yáng)明的故事,話(huà)“度”的人生學(xué)問(wèn)。
(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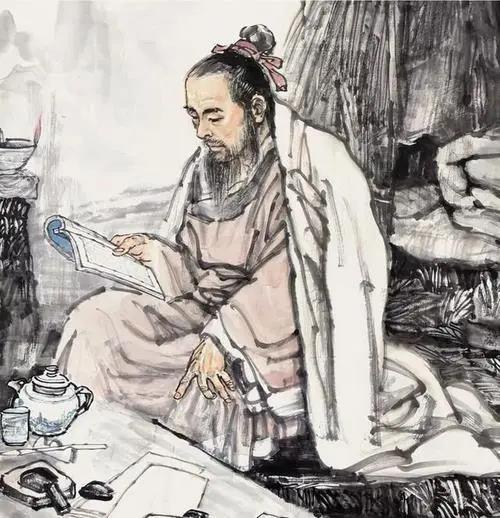
在中國(guó)歷史上,王陽(yáng)明的知名度仿佛有東山再起之勢(shì)。當(dāng)然,王陽(yáng)明的觀點(diǎn),相當(dāng)有個(gè)性。王陽(yáng)明(1472―1529),本名王守仁,字伯安,浙江寧波余姚人,世稱(chēng)陽(yáng)明先生,為我國(guó)明代著名哲學(xué)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和軍事家,有的還說(shuō)是思想家。他繼承發(fā)揚(yáng)儒家思想,創(chuàng)立陽(yáng)明心學(xué)(陽(yáng)明心學(xué)的三大核心:心即理,知行合一,致良知)。挑戰(zhàn)并打破宋明時(shí)期官方統(tǒng)治思想―程朱理學(xué),為儒學(xué)思想的又一文化高峰。陽(yáng)明心學(xué)影響深遠(yuǎn),曾國(guó)藩、梁?jiǎn)⒊仍S多名人的精神導(dǎo)師。并遠(yuǎn)播日本等國(guó),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(chǔ)。
有關(guān)資料記載,王陽(yáng)明五歲才開(kāi)口說(shuō)話(huà),一開(kāi)口不是叫爸爸媽媽?zhuān)潜痴b《大學(xué)》。十二歲時(shí)問(wèn)老師,“何為天下第一等事?”并說(shuō):“嵬科高第時(shí)時(shí)有,豈是人間第一流?!”“唯為圣賢,方是第一。”瞧不起狀元爸爸的狀元。十七歲結(jié)婚,新婚之夜閑逛到道觀,竟然忘了洞房中的新娘,和一位老道士談了一夜。二十八歲進(jìn)士及第,全國(guó)第十名,開(kāi)始從政生涯。四十七歲因功被封為新建伯。三十多歲開(kāi)始講學(xué),無(wú)論是當(dāng)官,被貶,閑賦在家,還是行軍打仗,總是不忘講學(xué),“倡明圣學(xué)為事”,講學(xué)是第一要?jiǎng)?wù)。五十六歲去世,謚號(hào)文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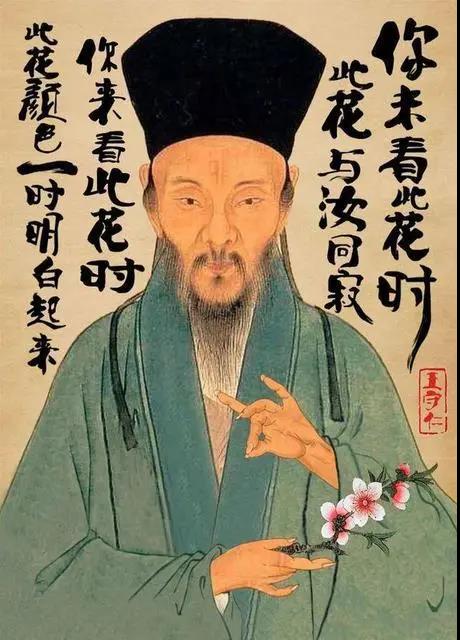
王陽(yáng)明在哲學(xué)上提出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的命題,沖擊了僵化的程朱理學(xué),最終集“心學(xué)”之大成。“陽(yáng)明心學(xué)”的思想本質(zhì)是強(qiáng)調(diào)個(gè)性化的發(fā)展、個(gè)人意愿的尊重及個(gè)體創(chuàng)造力的調(diào)動(dòng),至今仍有很強(qiáng)的現(xiàn)實(shí)意義。王陽(yáng)明“致良知”的思想內(nèi)涵,是把一定的社會(huì)道德規(guī)范轉(zhuǎn)化為人的自覺(jué)的意識(shí)和行為,強(qiáng)調(diào)主觀立志和主體精神的力量,強(qiáng)調(diào)人的自我更新,倡導(dǎo)學(xué)習(xí)要自求自得。致良知說(shuō),包括體認(rèn)和實(shí)現(xiàn)兩個(gè)層面。體認(rèn)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自我修養(yǎng),用現(xiàn)在的話(huà)來(lái)說(shuō)是指人對(duì)自身的道德認(rèn)知和情感的體驗(yàn)過(guò)程。實(shí)現(xiàn)良知?jiǎng)t是指人的思想和情感見(jiàn)之于行為的過(guò)程,即為規(guī)范道德行為和端正人生態(tài)度的實(shí)踐過(guò)程。王陽(yáng)明反對(duì)朱熹的“知先行后”說(shuō),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說(shuō)。他認(rèn)為知之真切篤實(shí)處,即是行,行之明覺(jué)精察處,即是知。強(qiáng)調(diào)一念發(fā)動(dòng)處便即是行,要人們?cè)谛摒B(yǎng)上防于未萌之先,克于方萌之際,重視對(duì)意念的克制工夫。
王陽(yáng)明堅(jiān)持我國(guó)古代儒家教育的傳統(tǒng),把道德教育與修養(yǎng)放在首位。關(guān)于道德修養(yǎng)的方法。王陽(yáng)明早年提倡靜處體悟。他認(rèn)為道德修養(yǎng)的根本任務(wù)是“去蔽明心”,即去除物欲的昏蔽,發(fā)明本心所具有的“良知”。道德修養(yǎng)無(wú)須“外求”,而只要做靜處體悟的功夫。晚年提出事上磨煉。他認(rèn)識(shí)到一味強(qiáng)調(diào)靜坐澄心,會(huì)產(chǎn)生各種弊病,容易使人“喜靜厭動(dòng),流入枯槁之病”,甚至使人變成“沉空守寂”的“癡呆漢”。改而提倡道德修養(yǎng)必須在“事上磨煉”。主張省察克治。他主張要不斷地進(jìn)行自我反省和檢察,自覺(jué)克制各種私欲。強(qiáng)調(diào)貴于改過(guò)。他認(rèn)為人在社會(huì)生活中總會(huì)發(fā)生這樣或那樣一些違反倫理道德規(guī)范的過(guò)錯(cuò),即是大賢人,也難以避免。在道德修養(yǎng)中,不貴無(wú)過(guò),而貴改過(guò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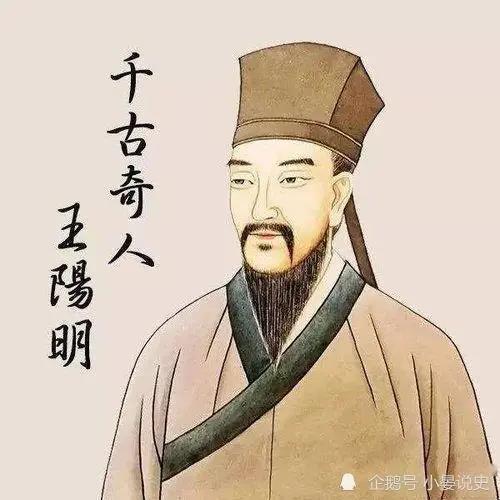
王陽(yáng)明提出“隨人分限所及和益精其能”說(shuō)。主張施教要照顧學(xué)生的心理發(fā)展水平。他認(rèn)為一個(gè)人從嬰兒到成人有其發(fā)展的階段性,比如種植樹(shù)木,須栽培得宜,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(jìn),才能取得成效。他提出人的資質(zhì)是不同的,施教須隨人分限所及,因人而異,不可躐等;人的才能也互不相同,使他們益精其能,是學(xué)校教育的重要任務(wù)。這一學(xué)說(shuō),用現(xiàn)在的話(huà)來(lái)說(shuō)就是分層教學(xué)和發(fā)展學(xué)生個(gè)性特長(zhǎng),讓每個(gè)學(xué)生都得到最優(yōu)化發(fā)展。
王陽(yáng)明在施教方法上主張樂(lè)習(xí)不倦。他竭力反對(duì)一味督責(zé)、鞭撻繩縛的教學(xué)方法,要求教學(xué)者考慮到學(xué)生樂(lè)嬉游而憚拘檢的心理特點(diǎn),否則就會(huì)出現(xiàn)學(xué)生視學(xué)舍如囹獄而不肯入,視師長(zhǎng)如寇仇而不欲見(jiàn)的局面。王陽(yáng)明還提倡教學(xué)中要?jiǎng)屿o搭配,使學(xué)生趨向鼓舞,中心喜悅,從而樂(lè)習(xí)不倦。
(二)

我們現(xiàn)代人也需要向王陽(yáng)明學(xué)做人做事,要守好五個(gè)“度”,方能把握好人生大方向。努力做到:胸懷有寬度,辦事有力度,讀書(shū)有厚度,眼界有高度,說(shuō)話(huà)要適度。
第一,胸懷有寬度。
佛家喜歡論“境界”,按照儒家的說(shuō)法叫“胸次”。王陽(yáng)明講,做人應(yīng)當(dāng)“胸次悠然”。王陽(yáng)明是個(gè)性情中人,平生主張盡性而為。在他看來(lái),一切本該順其自然。太過(guò)糾結(jié)在意,反倒成了內(nèi)心的障礙。王陽(yáng)明說(shuō):“過(guò)去未來(lái)事,思之何益?徒放心耳。”過(guò)去事放不下,未來(lái)事想不通。胸次漸窄,人也就走進(jìn)了死胡同,是謂“著相”。懂得享受當(dāng)下生活的人,對(duì)于過(guò)去的得失,不做無(wú)謂的計(jì)較;對(duì)于未來(lái)尚未發(fā)生的事情,也不做杞人憂(yōu)天的擔(dān)心。他們胸懷寬闊、內(nèi)心清明,所以他們是快樂(lè)的。莊子云:“虛室生白,吉祥止止。”空的房間才顯得敞亮,吉祥的事情才能容納進(jìn)來(lái)。人的胸懷也是這樣,王陽(yáng)明說(shuō):“草有妨礙,理亦宜去,去之而已;偶未即去,亦不累心。”只有拔除胸中的雜草,去除那些無(wú)謂的煩憂(yōu),才能常保安寧祥和。
第二,辦事有力度。
王陽(yáng)明是心學(xué)宗主,卻也是一位實(shí)干家。在他看來(lái),任何成就都不是憑空想來(lái)的。要想取得一番大成就,必得先下一番苦功夫。如果做得不夠好,一定是功夫下得還不夠深。只要工夫深,把該做的事都做好了,一切便會(huì)不求自來(lái)。王陽(yáng)明自己不滿(mǎn)足于紙上談兵,一有機(jī)會(huì)就實(shí)踐自己的兵法功夫。他曾以欽差的身份,奉旨督造一項(xiàng)工程。王陽(yáng)明以兵法統(tǒng)御之方,對(duì)工程隊(duì)實(shí)行軍事化管理。他組織民工演練“八陣圖”,讓民工勞逸結(jié)合,按時(shí)作息。對(duì)待手下的管理人員,也以兵法約束和指揮。在他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,工程隊(duì)的效率遠(yuǎn)勝平常。等到工程建設(shè)完畢,他對(duì)兵法的領(lǐng)悟也更深了。王陽(yáng)明說(shuō):“人須在事上磨,方立得住,方能‘靜亦定,動(dòng)亦定’。”在他看來(lái),說(shuō)話(huà)有說(shuō)話(huà)的功夫,辦事有辦事的功夫,這些都得在事上磨練。功夫下得越深,根基也就扎得越穩(wěn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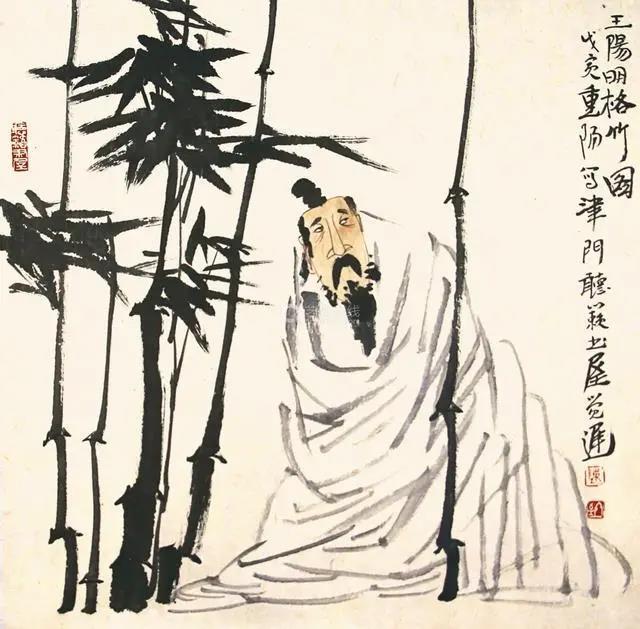
第三,讀書(shū)有厚度。
王陽(yáng)明認(rèn)為,讀書(shū)是為了積累人生的厚度。有些人腦袋空空、腹內(nèi)草莽。無(wú)法在世間做出絲毫貢獻(xiàn),對(duì)于自己的人生也全無(wú)益處。莊子曰:“水之積也不厚,則其負(fù)大舟也無(wú)力;風(fēng)之積也不厚,則其負(fù)大翼也無(wú)力。”凡有大志向的人,必定注意累積自己讀書(shū)的厚度。從書(shū)本中汲取的知識(shí)越厚重,遇到困難解決的辦法也會(huì)多一些。王陽(yáng)明說(shuō),書(shū)一定要多讀,但不強(qiáng)求全部記住。多讀經(jīng)典不僅是為了開(kāi)啟智慧,更是為了在反復(fù)思索中存養(yǎng)本心。英國(guó)哲人培根說(shuō):“讀史使人明智,讀詩(shī)使人聰慧,哲理使人深刻,道德使人有修養(yǎng),邏輯使人善辯。”每讀一種書(shū),便能收獲一種的好處。有了知識(shí)的托舉,人生便如順?biāo)兄邸⒁硐律L(fēng)。
第四,眼界有高度。
人的眼界,決定了起點(diǎn)。不管做事還是做人,都應(yīng)往更高更遠(yuǎn)處看。王陽(yáng)明十三歲時(shí),就向私塾先生發(fā)問(wèn):“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?”老師回答他:“讀書(shū)考狀元便是天下第一等事。”王陽(yáng)明卻不以為然地說(shuō):“考狀元不算什么,讀書(shū)做圣賢才是天下第一等事。”唐太宗曾說(shuō):“取法于上,僅得為中;取法于中,故為其下;取法于下,則無(wú)所得矣!”意思是說(shuō),想要做到的是一流,最后所能做到的不過(guò)是中流;想要做到的是中流,最后所能做到的不過(guò)是末流;想要做到的是末流,最后可能什么都做不到。要有高于尋常的眼界,才能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。
第五,說(shuō)話(huà)要適度。
中國(guó)人講究“出言有尺,說(shuō)話(huà)有度”,其實(shí)就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分寸感。言語(yǔ)多寡不能定高下,而一旦越界卻勢(shì)必傷人害己。王陽(yáng)明說(shuō):“大凡朋友,須箴規(guī)指摘處少,誘掖將勸意多,方是。”與朋友對(duì)話(huà),不宜當(dāng)面指責(zé)對(duì)方的過(guò)失。可以選擇委婉地表達(dá),才是更容易被接納的做法。古人說(shuō):“知人不必言盡,言盡則無(wú)友。責(zé)人不必苛盡,苛盡則眾遠(yuǎn)。”把握說(shuō)話(huà)的分寸,守好言語(yǔ)的邊界。既是對(duì)別人的尊重,也是對(duì)自己的保護(hù)。
(三)

關(guān)于“度”的學(xué)問(wèn),需要學(xué)習(xí)一生,感悟一生。惟寬可以容人,惟厚可以載物,守“度”是人生大智慧。這些“度”,人們讀懂了幾個(gè)?
以時(shí)髦的詞“格局”有高度為例。很多事情,不是從智商和學(xué)識(shí)來(lái)劃分的,而是從格局開(kāi)始的。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諺語(yǔ):再大的烙餅,也大不過(guò)烙它的鍋。一個(gè)人能取得多少成就,過(guò)怎樣的人生,取決于這個(gè)人的格局和視野的大小。大事難成,往往因格局太窄。
作家劉墉曾在自己的書(shū)里分享了這樣一則故事:大學(xué)時(shí)期的同學(xué)跟他抱怨老板,自己做著累死累活的工作,卻只給一丁點(diǎn)兒工資,還故意拖延他的綠卡申請(qǐng)。劉墉聽(tīng)完,故意和同學(xué)說(shuō):“這么壞的老板,你怎么能白干這么久,你要多學(xué)習(xí)一點(diǎn)東西再跳槽,這樣才不虧。”同學(xué)覺(jué)得劉墉說(shuō)的有道理,于是天天主動(dòng)加班,學(xué)習(xí)各種商業(yè)文書(shū)的寫(xiě)法,甚至還學(xué)了修復(fù)印機(jī)的技能,想著以后自己創(chuàng)業(yè)了省一筆維修費(fèi)。就這樣過(guò)了半年,劉墉又問(wèn)同學(xué):“你跳槽了嗎?”同學(xué)笑著說(shuō):“我現(xiàn)在升職加薪了,老板對(duì)我刮目相看,我干得開(kāi)心,不跳槽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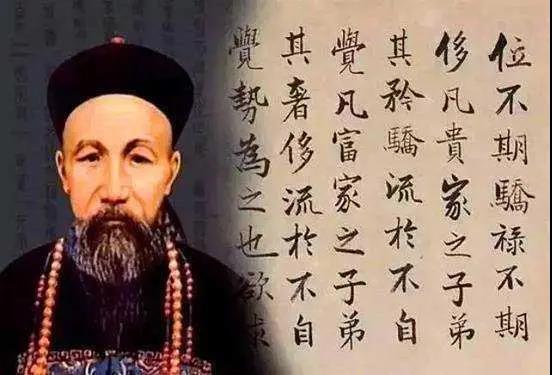
能將自己格局放開(kāi),轉(zhuǎn)化心態(tài),就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生活哪有那么多煩心事和不公平。如果能以主人公的心態(tài)來(lái)對(duì)待事情,就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很多困難都是讓自己學(xué)習(xí)成長(zhǎng)的經(jīng)歷罷了。如果總是拘泥于一念,無(wú)法打開(kāi)格局,只會(huì)讓路越走越窄;而轉(zhuǎn)換心態(tài)與思維,將格局放大,就能有全新的視野,成就新的舞臺(tái)。曾國(guó)藩曾有句名言: “謀大事者,首重格局。”站得更高,看得更遠(yuǎn),想得更長(zhǎng)久,讓格局寬大起來(lái),才能將路走得更遠(yuǎn)。總結(jié)人生,人們不僅要學(xué)出名堂來(lái),更要明白這其中的道理:用寬廣的胸懷去對(duì)待別人;用妥帖的言語(yǔ)同他人溝通;用讀好書(shū)來(lái)充實(shí)精神;用大格局面對(duì)生活窘境。
一定意義上說(shuō),度是哲學(xué),度是心理學(xué),度是社會(huì)學(xué),度是生命學(xué)。人生需要認(rèn)識(shí)“度”,因?yàn)槊恳弧岸取倍际且婚T(mén)學(xué)問(wèn)。人生的船是自己掌舵的,只有堅(jiān)守這些“度”,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(yùn),把路走得越來(lái)越寬、越來(lái)越直。愿人們也能明白這些“度”背后的意義,無(wú)論生活在何處,都能用心中的尺度把握人生。王陽(yáng)明關(guān)于“度”的學(xué)問(wèn),誨人不倦!
秦寄翔








